2023年,杂货商Winn-Dixie提请的反垄断诉讼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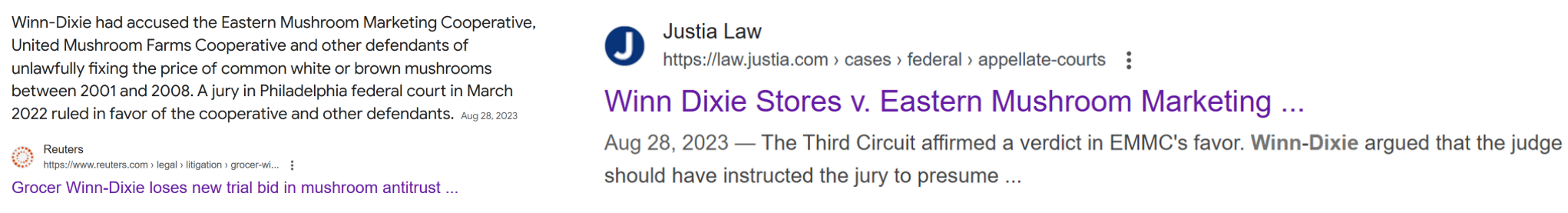
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给的判决书不长,其中将近一半的篇幅被用于探讨quick look分析法是否能适用于本案。当然,最终的结论很无情:
As for whether this unique, integrated hybrid scheme sufficiently resembles a purely horizontal or vertical arrangement, we conclude that it falls in between, so the rule of reason applies. 至于这个独特的、综合的混合方案是否足够类似于纯粹的水平或垂直安排,我们认为它处于两者之间,因此适用于合理规则。
为什么quick look的适用失败值得被写进新闻?为什么联邦法院和上诉法院都将quick look的分析作为绝对的重点?这种分析是必须的吗?
以及,为什么说quick look有“原罪”?
为了讲清楚这一切,需要先从quick look是什么开始,而为了讲清这个问题,又要从合理分析法和本身违法原则的兴衰讲起。
合理分析&本身违法
历史上,美国的反垄断案件主要有两个分析框架。本身违法原则假定某些类型的行为本身就是反竞争的,法院无需对其市场影响进行详细分析,只要能证明行为的存在即可。合理分析法则谨小慎微得多,法院需要对特定行为的影响进行详细分析,考虑市场力量、潜在危害、可能存在的正当理由等,相当复杂。
法庭适用的方法往往是从繁到简,这里也不例外。
《谢尔曼法》第1条禁止“任何以契约、托拉斯或其他形式之结合、或共谋,限制美国各州间或与外国间之贸易或商业者,均属违法。 ”但是,市场上的诸多行为都会对贸易或商业构成限制,《谢尔曼法》的用语又过于模糊。法院于是通过司法判例确定,需要被处罚的只有“不合理的限制”。为了确定案涉行为是否会抑制竞争,合理分析原则应运而生,并长期作为默认路径而存在——如无特殊情况,则合理分析。
著名案例Ohio v. American Express中,法院确定了合理分析原则的“三步举证责任转移框架(a three-step, burden-shifting framework )”。
首先,原告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证明案涉行为对相关市场的消费者造成了实质性的反竞争影响。因此,原告通常需要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否则将无法衡量被告造成的影响。
被告造成的影响可以用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来证明。直接证据如在相关市场上的产量减少、价格上涨或质量下降,间接证据则往往需要借助“市场力量”等概念完成证明。
随后,举证责任发生转移,被告需要说明案涉行为的正当理由。
完成该等说明后,举证责任再次转移给原告,要求其证明被告的理由不足以支撑其行为。换言之,同样的目的可以通过其他对竞争的损害更轻微的手段实现。
合理分析原则的复杂性让诉讼变得更为冗长,因而法院开始试图做出一些简化。1940年,“本身违法”的表述正式出现在最高法院的裁定中。1958年的北太平洋铁路案中,最高法院进一步做出了解释:
there are certain agreements or practices which because of their pernicious effect on competition and lack of any redeeming virtue are conclusively presumed to be unreasonable and therefore illegal without elaborate inquiry as to the precise harm they have caused or the business excuse for their use. This principle of per se unreasonableness not only makes the type of restraints which are proscribed by the Sherman Act more certain to the benefit of everyone concerned, but it also avoids the necessity for an incredibly complicated and prolonged economic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industry involved, as well as related industries, in an effort to determine at large whether a particular restraint has been unreasonable—an inquiry so often wholly fruitless when undertaken.
设定本身违法原则的初衷是好的。一方面,增强了《谢尔曼法》执法的确定性——合理分析原则的另一面是个案分析,而本身违法原则则直接很多。另一方面,免除了法院以及原被告的经济调查之苦。
然而,市场竞争是复杂多变的,本身违法原则的弊端很快显现了出来。在不审查实际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假定存在反竞争效果的结果便是,一些明明有利于市场竞争的行为被判违法,招致了众多批评。
1977年的GTE Sylvania案中,最高法院首次对本身违法原则过度适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法院认为,被告将独占区域分配给经销商的行为并不隶属于本身违法原则,因为这种限制可以确保经销商获取足够的利润,进而促进品牌间(intrabrand)竞争。在这一前提下,牺牲品牌内(interbrand)竞争是可以理解的。
法院的分析细化到这一层面后,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便越来越难了。即使是典型意义上的违法行为,如竞争对手的横向联合,也逐渐被归入合理分析的范畴,法院需要判断相关的限制是否与合法的竞争目的有关。为了作出该等判断,法院依然需要对市场进行调查。由此,逐渐背离了设定本身违法原则的初衷,重新回到了繁琐的合理分析至上时代。
快速检视
源起
合理分析原则和本身违法原则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繁,一个极简。
快速检视的诞生与法院对本身违法规则逐渐持谨慎态度的趋势密切相关。
先是Burger法官在Topco案中提出了异议,认为虽然本身违法原则能够提高司法效率,但它不应当以妥协谢尔曼法的总体政策目标为代价。随后,最高院逐步采纳了这种谨慎的立场。Continental v. GTE-Sylvania案中,法院认可了电视制造商对零售商之间的区域市场分配,因为它能促进品牌之间的竞争。这种谨慎又扩展到了传统的横向限制行为,例如,BMI v. CBS案中,法院拒绝了对音乐表演者、作曲家和出版商之间的统一许可协议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并指出,该协议是“辅助性的”,因为它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增加了整体的消费者福利。Northwest Wholesale Stationers, Inc. v. Pacific Stationery and Printing Co.案中,法院甚至对联合抵制(group boycotts)和捆绑销售(tying arrangements)也表现出了更加宽容的态度。这种态度上的转变,为快速检视原则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就像没有非黑即白一样,大量的市场行为既没有严重到存在即违法,也没有轻微到足以适配全面而复杂的合理分析法。除了在这两端之间摇摆不定,法院开始探索一条折中的“第三条路”,介于两者之间的“快速检视”(quick look)应运而生。
理论上,快速检视适用于反竞争效果十分明显的案件。它们在类别上不能归入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但足够符合经济直觉。用最高院的表述来说,合理原则有时可以在眨眼之间得到适用(the rule of reason can sometimes be applied in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快速检视的逻辑大致可以描述为:明显的反竞争效果→触发存在反竞争影响的假设→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要求其提供正当理由。
然而,反竞争效果的明显程度应当达到何种地步呢?最高法院表述如下:
To use the “quick look” approach, we must first determine whether “an observer with even a rudimentary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s could conclude that the arrangements in question would have an anticompetitive effect on customers and markets.“ Once it is established that the restraint is inherently suspect and the anticompetitive effects are easily ascertained, then the burden shifts to the [defendants] to produce evidence of procompetitive justification or effects and thus demonstrate the need for more extensive market inquiry, . . .
也就是说,反竞争效果的明显程度需要足以让一个对经济学只有最基础的了解的人也能发现。
当然,这依然是个非常模糊的标准。
三起重要案件
快速检视的发展有赖于三起最高院案件——专业工程师协会案、NCAA案和印第安纳牙医协会案。
专业工程师协会案经常被原告引用,用于支持快速检视的适用。这起案件中,专业工程师协会发布了一项伦理准则,禁止工程师参与竞争性投标,不允许他们披露价格,以防客户基于价格而非专业性做出决策。本案的实质其实和快速检视联系不大——工程师们在辩护中直接承认了自己的行为有害竞争。他们认为,竞争性投标不符合公众利益,因为它可能会导致虚假的低价,进而诱使个别工程师交付劣质的工作,危及公众健康。最高法院驳回了这一理由,并做出了著名的表述:
the Rule of Reason does not support a defens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competition itself is unreasonable
专业工程师协会案之所以和快速检视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人们认为,本案中出现的并不是价格固定等典型的违法行为,然而法院并不需要通过复杂的行业分析来证明案涉行为的反竞争特征。
NCAA案中,被告限制了每一所大学所能转播的橄榄球比赛次数,以及可以转播的大学比赛的总数。地区法院认为该等做法是对法律的违背,第十巡回法院大体确认了地区法院的结论,做出了少量修改。最高法院则认为,虽然NCAA制定的规则构成水平价格固定以及限制产出的行为,但这种限制是必要的,否则体育联盟将会无法运作,因为各个队伍将会永远无法达成一致。
既然限制的存在是有必要的,本身违法原则自然不能适用了。在合理分析的过程中,法院将市场界定为大学橄榄球赛,NCAA在这一市场中几乎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因而具有市场权力(market power)。它制定的规则减少了产出(转播的橄榄球比赛数量),提升了购买版权所支付的价格。
NCAA案和快速检视之间的关系来源于市场权力部分。法院指出,证明案涉协议的反竞争特征无需经过复杂的行业分析。因而,原告不需要在任何被精确定义的市场中建立市场权力。“合理原则有时可以在眨眼之间得到适用”的说法也出自于本案。
印第安纳牙医协会案与保险公司有关。当时的健康保险公司会对医疗流程进行审查,并拒绝赔付它们认为没必要的部分。为了阻止这种审查,许多印第安纳州的牙医以及一个行业协会达成了协议,决定不再向保险公司提供X光片。
本案中,最高院拒绝适用本身违法的原则。但是,从合理分析的角度来看,牙医协会仍然难辞其咎。一方面,明显存在拒绝提供信息的横向协议,另一方面,存在实际损害(X光片不可用),且没有正当理由。部分评论家认为,原告在没有对市场进行定义的情况下赢得胜诉,是因为最高院实质性地使用了快速检视。
这三起案件是美国反垄断法以及快速检视历史上鼎鼎有名的重要案件。吊诡的是,没有一起正式提到“快速检视”。甚至,最高院看起来并不认为这些案件的审查过程与快速有任何联系可言。专业工程师协会案中的双方“整理了大量的发现和审判记录……地区法院进行了详细的裁决”;NCAA案的初审法院进行了全面审查,写了53页判决书;印第安纳牙医协会案中,法院进行合理分析的前提是原告FTC呈递的海量证据。换句话说,原告的胜诉与快速检视并无关联——他们仍然是通过大量的证据说服法院的。
基于这些,重新回到这三起重要案件,我们会发现,比起“最高院应用了快速检视”这一论断,似乎能从中得出的更直接、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是“证据确凿时,做出判决会更简单”。
如果秉持这个观点,那么美国最高院迄今为止没有在任何案件中适用过快速检视。
反对快速检视
明确支持快速检视的最高院案例没有,反对的倒是不少。从措辞上看,美国最高院对快速检视的方法抱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奈何在每个案件中都认为不适宜采用这种方法。
加利福尼亚牙科协会案中,美国最高院首次提及了“快速检视”这一术语。和专业工程师协会类似地,加利福尼亚的牙科协会也发布了一个伦理规范,禁止虚假或具有诱导性的广告。原告是FTC(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联邦贸易委员会),认为牙科协会的伦理规范实质上不正当地限制了牙医们通过广告展示自己在价格或质量方面的优势。FTC和上诉法院的裁定中,运用的都是快速检视法。
然而,到了最高院之后,法院先是回顾了前文提到的三个重要案件,声明在这些案子中,即使是对经济学只有基础理解的观察者,也能认识到相关的安排会对顾客和市场产生反竞争影响。在牙科协会案中,广告限制“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了虚假或误导性的广告,……,可能被认为对竞争产生积极影响,或者对竞争根本没有影响”。因此,法院撤销了FTC做出的裁决,并将案件打回下级法院,要求进行全面的审查。重审后,第九巡回法院认定该广告限制合法。
Texaco案同样与第九巡回法院有关。
Texaco和Shell石油公司曾是美国西部汽油销售的竞争对手。1998年,它们创立了一个合资企业Equilon。原告指出,Equilon为Texaco和Shell品牌的汽油设定了统一价格,构成价格垄断,得到了第九巡回法院的支持。
美国最高院推翻了第九巡回法院的判决,认为没有证据Equilon本身是违法的,而如果合资企业的成立是合法的,那么它为自己的产品定价并不违法。
though Equilon’s pricing policy may be price fixing in a literal sense, it is not price fixing in the antitrust sense 尽管Equilon的定价政策在字面上可能是价格操纵,但在反垄断意义上并不是价格操控
这份裁决的篇幅很短,脚注中提及了快速检视。最高院指出,快速检视可能可以适用于其他案件,但Texaco案不在此列。
To be sure, we have applied the quick look doctrine to business activities that are so plainly anticompetitive that courts need undertake only a cursory examination before imposing antitrust liability. But for the same reasons that per se liability is unwarranted here, we conclude that petitioners cannot be held liable under the quick look doctrine.
的确,我们曾将快速检视原则适用于那些显然反竞争的商业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只需进行简要审查便可判定反垄断责任。但与本案中不适用法定责任的理由相同,我们认为申请人不能依据快速检视原则被判定承担责任。
Actavis案的背景相对复杂一些,涉及“付费延迟(Pay-for-Delay)”协议是否构成市场分割行为。
“付费延迟”指的是品牌药品制造商向仿制药制造商支付一定的金额,以换取后者推迟或延迟推出仿制药产品。这种做法可以确保品牌药在一段时间内的市场独占地位,避免与价格更低的仿制药竞争。
原告认为,这种协议是默认违法的,构成市场分割。法院则认为,需要考虑是适用快速检视还是合理原则。
there is always something of a sliding scale in appraising reasonableness 在评估合理性时,总是存在一定的滑动尺度
最高院在NCAA v. Alston案中,再次采用了与“滑动尺度”类似的语言,实质上削弱了快速检视作为一种独立分析方法的分量。
what is required to assess whether a challenged restraint harms competition can vary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The whole point of the rule of reason is to furnish an enquiry meet for the case, looking to the circumstances, details, and logic of a restraint
评估所挑战的限制是否损害竞争所需的分析,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不同。合理规则的核心就在于,提供一个适应具体案件的审查方法,考虑限制的具体情况、细节和逻辑。
NCAA也算是法庭常客了。Board of Regents案中,限制足球比赛转播的规则被判违法。Alston案中,限制学校可向学生运动员提供的教育相关福利的规则再次被禁止。
地区法院采用了合理分析原则,双方提供了专家证人和大量证据,最终做出了详细的裁定。因而,摆在最高院面前的是明确的事实:第一,NCAA在相关市场中是垄断者。第二,案涉限制是在横向竞争者之间达成的。第三,限制措施降低了学生运动员的报酬,“抑制了学生运动员参与相关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因此价格和数量都受到了压制。
最高院认为,某些限制明显不会损害竞争,以至于无需进行太多审查。但是,Alston案中的事实不能允许任何一方“瞬间获胜”,必须进行更详细的分析。规则的合法性不意味着NCAA实行的所有行为都是合法的,鉴于原告提供了关于买方垄断以及对价格、产量产生不利影响的证据,快速检视不能取代本案地区法院采用的合理原则。
快速检视的“原罪”
距离快速检视原则被提出,已经过去了四十年。
最高院曾经充满希望地将它引入竞争法的领域,却注定要失望。上到最高院,下到各个地区法院,快速检查被一次次提起,却很少被适用。少量的适用案例中,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的又不在少数。经过了几十年的判例积累,美国司法体系仍然没有建立起针对快速检视原则的标准,以至于混乱的情形愈发严重。
快速检视原则如今已经负上“原罪”,代表着更冗长的程序、繁琐的举证、增加的争点。它为原被告增加了诉讼负担,让法院犹疑摇摆,举棋不定。它一次次出现,却总是带不来振奋人心的消息。这一切,与竞争领域的复杂性有关,与美国司法体系的特征有关,也与法院本身有关。
文章开头提及的Winn-Dixie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院不长的裁定中,一半篇幅用于解释为什么不能适用快速检视。裁定的措辞有时果断,有时又显得十分犹豫——法院自己也拿不准,快速检视原则究竟应当被作为一种简化版的合理分析,还是一个独立的分析类别。
美国司法体系所规定的证据开示带来的是海量证据的使用,从各类报告、文书,到专家证人、律师费用。创设快速检视原则的初衷,是帮助原告和被告节约合理分析所带来的巨大成本。然而,现在的快速检视成为了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偏偏又作用寥寥。原被告被迫在是否能适用快速检视原则这一问题上浪费多余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接着被法院告知要进入合理分析阶段。
作为一个判例法国家,判例在美国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然而,从本文前半部分介绍的判例来看,这些案例根本无法为后来者创造清晰可用的标准。快速检视近乎艺术而不是法律理论,像是一种只能凭感觉靠近的东西——“当我看到它时,我就知道它”。
法院在Winnie-Dixie案中也的确是这么说的:
If this sounds like a test of ‘I know it when I see it,’ that is not far from the mark. There is no set methodology for determining when the quick look applies, . . .
第三巡回法院承认,对于何时应当适用快速检视的问题,自己并不清楚。短短两句话,深深的无奈。
这种失败不是下级法院的过错——最高法院自己都表示:
The truth is that our categories of analysis of anticompetitive effect are less fixed than terms like “per se,” “quick look,” and “rule of reason” tend to make them appear.
最高院的站位更高,它对整个选择框架都态度犹豫。但是,对于实际处理案件数量更多的下级法院而言,快速检视原则带来的困境最棘手。合理分析原则虽然繁琐,但是它毕竟是安全、明确的。在不知道怎么做的情况下,深入分析反竞争效果总归不会有问题。类似地,本身违法原则或许武断,针对的是特定、明确类别的反竞争行为。问题就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地带,时至今日仍然像是一片美国反垄断法的荒地。用错了,就是方向性错误,势必会迎来重审。
地区法院针对同一类行为的看法本身存在矛盾,上下级法院之间也有分歧。例如,结合了横向和纵向因素的案涉行为,能否凭快速检视进行定性?第三巡回法院在Winn-Dixie案中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第六巡回法院则在Southeastern Milk案中留下了适用快速检视分析的空间。随后,上诉法院撤销了第六巡回法院的简易裁定,指示地方法院重新审查是否适合使用快速检视分析。
前文提及过快速检视的适用情形——某些行为具有明显的反竞争效应的情况下,即使是那些对经济学只有最基本的了解的人,也能看出这些行为会对消费者以及市场产生反竞争影响。这个标准的问题在于,一旦被告提出具有表面合理性的辩解,法院在对市场情况不够清楚的情况下,就会动摇,因为无法定义市场的整体效应。许多法官自己就是“对经济学只有基本了解的人”,但他们同时又担负着司法职能。快速检视又要提升效率,又不能承受违背谢尔曼法的政策目标的风险,结果左右为难,进退不得。即使法官对于被告提出的辩解存在“强烈顾虑”,也不敢轻易动用快速检视。
以上种种已经说明,快速检视并不会像最高院所期望的那样,节省事实发现阶段所需的时间和成本。Alston和Board of Regents案中,最高院的裁判“踩在了地区法院的肩膀上”。明确的事实已经摆在面前——横向定价协议、垄断力量、对价格的不利影响。最高院能一眼看出反竞争行为的原因是,地区法院已经做了大量的调查。
写到这里,两个问题自然地浮现。
第一,既然快速检视如此不堪,何必频频提起?置之不理,束之高阁,难道不可以吗?
快速检视的存在决定了它永远无法被边缘化。于原告而言,提出快速检视是一种诉讼策略,一个明智之举。因为,快速检视所暗含的假定是“案涉行为有明显的反竞争效应”。法院如果支持原告的快速检视诉求,那么可以说案子已经赢了一半。快速检视本身的模糊性,给原告们提供了乐观的空间——还是有可能启用的。对于被告而言,则会尽一切努力寻找证据,将自己从快速检视的范围中拉出来。
可以说,快速检视几乎和管辖权异议一样,成为了双方博弈的第一个战场。
第二,法官不懂经济学有什么可指摘的呢?法官不需要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只要能正确地适用法律即可。
是的,法官不需要做一个兼职经济学家,他们只需有效地运用一些法律技巧,例如推定、举证责任的转移。但是,这反而再次佐证了快速检视的矛盾。既然法官无法通过经济学推理得出直观的结论,合理测试就会始终被依赖。从这个角度而言,与其和原被告在快速检视上痴缠,还不如直接切入核心问题,从证据的质量、数量入手,或者在事实基础上判断,如何进行合理分析原则项下的举证责任转移。部分法院提及的“滑尺”标准,代表的其实就是这种倾向。
洗清快速检视的原罪几乎是不可能的——“错误地判定合法商业安排的成本尤其高,因为这会抑制反垄断法旨在保护的促进竞争行为”。
我对快速检视分析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