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世界里,我们的一举一动正在被记录、分析,并且变成一笔巨大的商业利润。
传统的个人信息保护依赖于“通知-同意”框架,事先披露所需要收集的信息类型、用途,征求用户的同意。
但是,扪心自问一下,你在第一次使用各种app的时候,真的会点开《用户协议》《隐私协议》,去看厂商如何处理你的数据吗?同意系统权限时,你会真的去了解一下app为什么需要这些吗?即使点开了,这么长的协议,普通人真的能弄明白吗?
数字企业对我们了如指掌,我们却对它们知之甚少,比如它们的运作模式、收集了哪些数据、如何使用这些数据,以及数据被分享给了谁。这就是信息不对称性。
而且,企业往往并不无辜。许多企业设计其用户界面,就是为了促使甚至鼓励用户公开信息。背后的原因很简单,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对企业而言是有利可图的。用户画像的精细化使广告投放转化率提升,电商平台通过浏览记录推荐商品,广告点击率可提高2-3倍。即使不用于营销,个人信息本身也是值钱的数据资产,转卖、加工都是利润丰厚的生意。
基于这样的困境,耶鲁大学法学院的Jack M. Balkin提出了一种新的设想——信义模式(The Fiduciary Mo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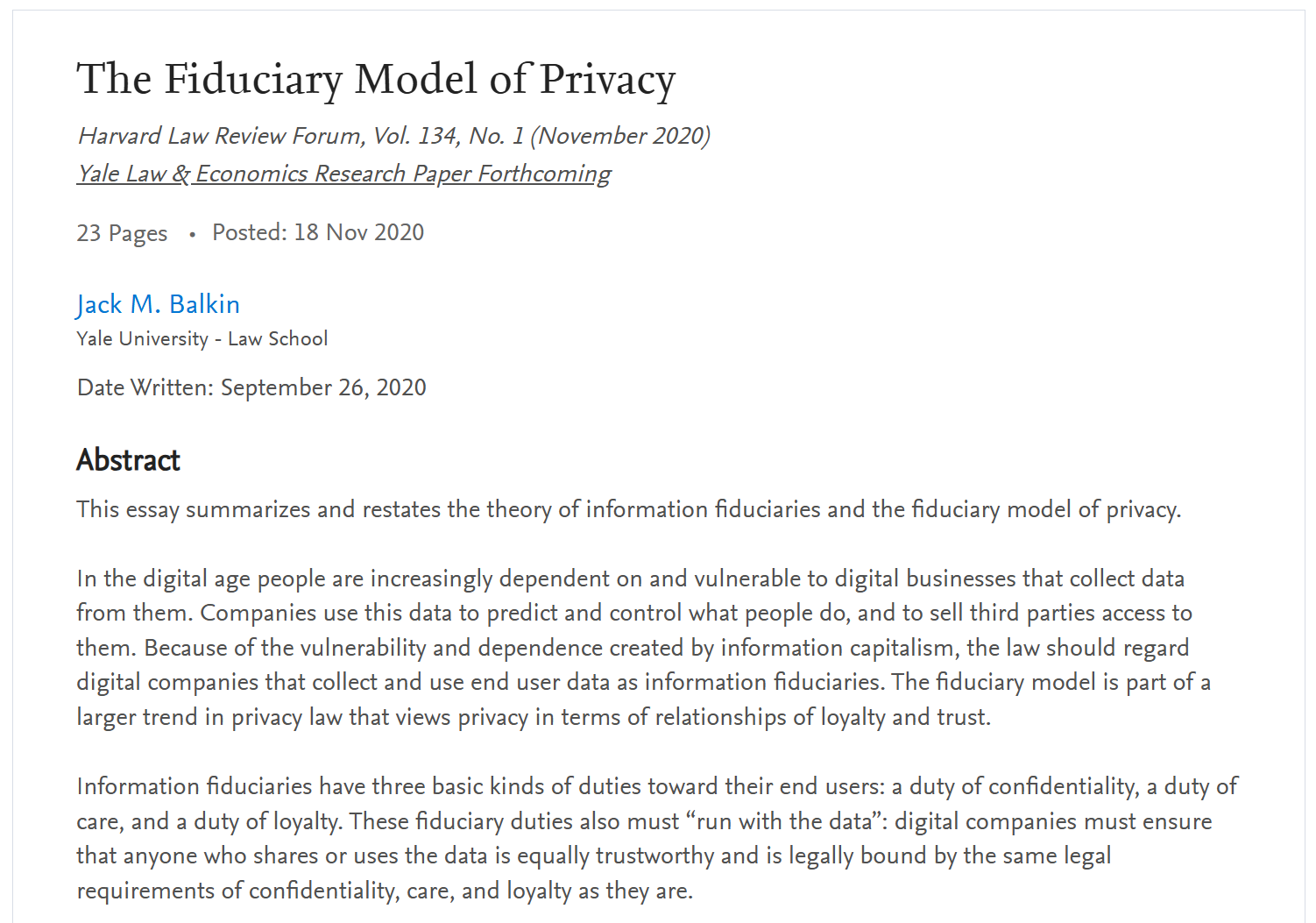
信义关系并不是新创设的法律概念,它本身是法律为保护弱势方在特殊权力结构中免受剥削而设立的特殊法律关系,核心特征在于不对等的权力结构和基于信任的脆弱性。传统的信义关系成立的前提是存在以下特征:
1)信任邀请,强势方(如医生、律师)通过明示或暗示行为诱导弱势方产生信赖。
2)权力失衡,一方拥有显著更多的信息、资源。
3)监督困难,弱势方无法有效监控强势方的行为。
4)依赖性,弱势方必须依赖于强势方才能实现特定目标。
相对应地,平台邀请用户同意自己的隐私政策,但拒绝展示算法以及数据处理的黑箱,用户难以开展有效监控。由于网络效应和垄断问题,人们往往必须使用特定的大平台,才能和周围的朋友保持联系。因此,传统的信义模型在数字时代仍有适用空间。
既然如此,下一个问题是:适用信义模型有什么好处?
首先,信义模型的实施使得数字企业对用户数据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和谨慎义务 。这要求数字企业不仅在自身范围内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和隐私,还必需在将数据分享或转移给第三方时,确保这些第三方同样遵守同等的保密和谨慎标准。
其次,通过“伴随数据而延续”的机制,信义义务被扩展至每一个接触或使用用户数据的第三方。这样,用户的数据不仅在初始提供给数字企业时得到保护,也在数据流通过程中始终受到严格的安全和合规管理。
最后,模型中的忠诚义务赋予了用户更高层次的保障。数字企业必须基于用户的利益设计和运营平台,避免与用户产生利益冲突。例如,他们不得通过操纵用户做出不理性行为来获取商业利益(如诱导成瘾行为)。这种义务保障了企业行为的道德底线。
总之,信义模型的好处在于,它通过系统化的伦理义务、法律保障以及企业责任,形成了一套贯穿整个数据链条的保护机制。作者展望了一个更公平的数据生态——在这个体系中,隐私不再是企业肆意牟利的牺牲品,而是值得守护的权利。
设想总归是美好的,但是面临一个全新的建构,心中总归会有不少疑问。
- 真的能实现吗?我不相信这些资本家。
作者提出的信托人模型似乎过于理想化。科技企业的管理层本质上对股东负责——他们的法律义务是为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强制承担保护用户隐私的信托义务,会不会带来无法调和的矛盾?
其实,类似的优先义务早有先例,比如在环境保护法等领域。企业面临环保要求可能增加成本,但这并未改变股东义务。法律只是通过明确义务优先性,来平衡公共利益与公司获利。联邦隐私法可以明确规定“用户隐私优先”规则。这样,信托义务不再是企业遵守股东义务的障碍,而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企业可能会做一些面子工程来规避。
即使通过了联邦隐私法,从实践的角度来看,信息信托人模型是否可能落地?企业能够轻松规避监管,比如通过复杂的法律条文或将用户协议埋在长篇条款中,让人无从选择。
企业规避合规的能力确实很强。而信义模型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通过繁琐的规则约束公司行为,而是以新意关系重新定义公司与用户之间的框架。这不再是用户‘选择接受或失去服务’的单向关系,而是企业不得以任何形式规避履行信托义务的双向关系。
- 定向广告的商业模式始终与用户利益冲突,这种模型真能改变现状吗?
即便有信托义务,企业亦会以‘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广告服务’为借口继续侵害隐私。
在信义模式之下,定向广告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处于严格的约束之下。那些有害的,滥用信息推送来操控用户心理的广告将被杜绝。而那些能帮助用户找到感兴趣的、相关的信息,则会得到保留。信义义务的作用在于,通过赋予用户对广告模式更清晰的选择权,企业将不得以牺牲隐私为代价获利,并尝试更透明的选择。
- 针对科技巨头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他们的垄断问题。
我们是否应当分清主次,先处理市场集中的问题?
大型数字企业的权力确实来源于多领域法律和政策交汇的后果,不是单一隐私问题。但隐私信义模型本身并不与反垄断改革相冲突,而是可以在多个法律框架下协同推进。过度依赖某一政策工具反而可能导致其他领域的忽视,对竞争法或隐私保护而言,这一点是一样的。
这篇文章逻辑完善,通俗易懂,穿插了众多对批评者的回应,读来是一种享受,它所提出的信义模型,也令人眼前一亮。但在钦佩之余,也为我们留下了几个问题。
第一,作者讨论的似乎更多是垄断巨头。针对小型互联网企业,用户往往并没有“必须使用”的理由。在文章中,作者取巧地使用了网络效应作为论证,但这一依赖型并不总是成立。传统的信义模型并没有引入竞争的维度,而是将医生、律师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然而,将巨型网络公司和小型公司一概而论似乎是不合理的。
第二,数据的流通在目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我们衡量企业的经济利益以及个人权益的时候,后者明显具有优先性。但是,如果涉及到公共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呢?在国际局势越发紧张的当下,如果要求数据共享的机构是政府主体,信义义务真的能像文中说的那样拓展到他们吗?
第三,作者提出了提升透明度的设想之后,没有过多地在这个方面展开。如果说数据的处理尚且有一定可能公开,那么算法的公开基本上是从技术上、商业上都不可能的。一方面,算法是核心的商业机密,TikTok的推送算法中一定设置了与个人信息有关的众多变量,但是他们不会公之于众。另一方面,算法本身是一个黑箱,就连程序员自己,都很难打开弄清楚里面发生了什么。
总之,信义模型是一个很有新意的模型,能全盘改变包括商业逻辑在内的现实情况。它虽然非常依赖于法律以及监管机构,而且可能面临诸多阻力,但如果最终能达成保护个人隐私的结果,那么一切都是值得尽力克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