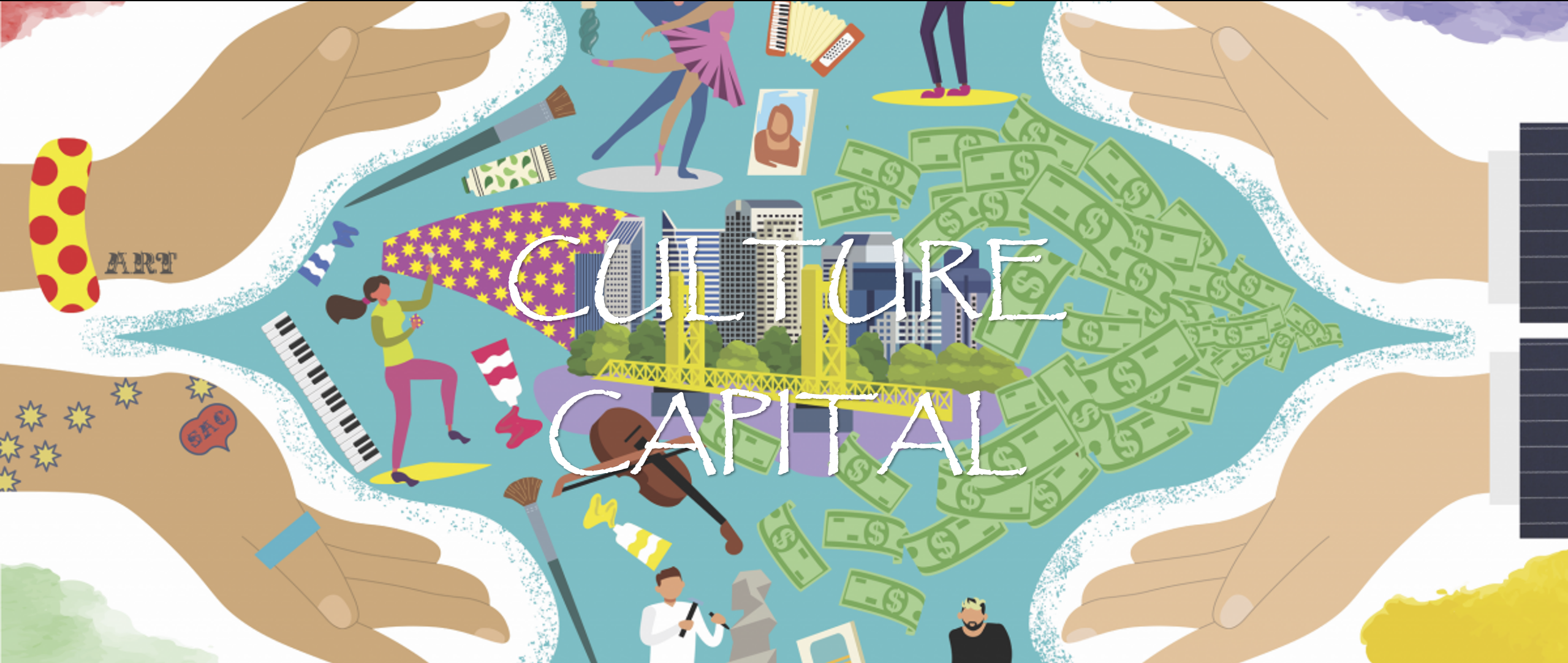目录
昨天洗碗的时候闲着没事,琢磨《学做工》这本书,想到“文化资本”的概念。
顺带指路之前的读书笔记:
简单来说,文化资本就是通过教育、文化背景、家庭环境等因素所积累的知识、品味、技能和社会习惯。这一整套东西,对于阶级身份的传递有重要作用。
《学做工》研究的是上个世纪的英国社会,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文化资本是什么?当信息差开始减少,外界的触角不断延伸,当高铁的票价下跌、出国不再是稀罕事,是什么在决定着所谓的阶级身份?
今天的中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要新增的要素或许是共同记忆、内驱力和对无聊的耐受度。
共同记忆的背后可能是某个固定的升学路径,从超级中学走出来的孩子继续走向寥寥几所固定的大学,或者兜兜转转来到同一家公司。他们不一定是同一届的,但是有东西可以说,孤身找工的时候领英上联系校友,说不定就有用。
记忆的锚点出现得越早,效果越好。大学不同系之间如有天堑,一个寝室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初高中则亲近许多,一代代的毕业仪式,每年都全体参与的活动,熟识的老师同学,都是打开话题的关键。但是,如果两个人来自同一个初高中,那么他们很可能住得不远,或者有着类似的家庭环境。这种可能存在的相似性,就是一种传递。
内驱力来自于教育和引导。
我最近意识到,有自己想做的、感兴趣的事情,可能也是一种文化资本。一个早早受到生计所迫的孩子,可能没有足够的空间来滋养兴趣和灵魂。越是挣扎,责任的分量越重,会超过兴趣和感受。睁开眼就想着今天怎么过活、家里怎么办的人,被迫对自己喜欢什么保持冷漠。
“对无聊的耐受度”直接就是一个伪说法。
世上的工作大多是无聊的,甚至是无聊又痛苦的。最底层的阶级身份通过“不挣钱怎么活”传递,稍微宽裕一点的家庭或许会从小就将孩子送去兴趣班,通过低阈值的训练帮助他们建立对无聊的耐受度。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将来能够静得下心,通过思考形成更稳定的心境或工作习惯。
最上层的特别有钱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我不知道。
当然,文化资本是很复杂的,还包括搜寻信息的能力、和人打交道的方式,甚至从小到大涉猎的文化、游戏作品,可能也应当囊括其中,相信每个人都能体会到。
我写这篇文章是非常忐忑的,因为很怕被错误地指认为一个阶级论者。所以我想继续花大约一半的篇幅再讲一个问题——没有这些文化资本,会怎样?
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原本来自阶级的研究。但是说到阶级,中国有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是不是一个存在精密内部划分的社会,以及在现在这个时代,阶级身份是否仍然重要到能取代个人身份,也是有待商榷的。
前段时间我看完了余华的《第七天》,里面有一条主线让我思考了很久。
鼠妹和伍超是一对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情侣,在理发店打工时认识。伍超小有天分,学什么都快。但是,为了保护鼠妹,他辗转打工时几次三番与店里的人起了冲突。此后,他便拒绝出去工作,宁可和鼠妹一起在最困顿的出租屋饿得前胸贴后背。
最后,鼠妹饿得受不了了,拉着他出门向人讨吃的。在一家面包店的门口,他们遇到了一个开奔驰的男人。
奔驰男很惊讶地打量了鼠妹几眼:“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怎么会沦落到讨东西吃?”
他提出了“帮助”鼠妹的想法,被鼠妹拒绝了,鼠妹只想要四个面包。
但是,余华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小说家,不会塑造一个纯洁无瑕的角色。鼠妹会抱怨自己为什么要找伍超,明明跟着别人就能过上更有钱的生活,她也会虚荣,会羡慕所谓的朋友的iphone手机。
在鼠妹生日这天,伍超送了鼠妹一部假的iphone手机,然后就回老家探病了。鼠妹备受打击,几次通过qq空间喊话伍超都没有得到回应。她无法接受伍超的欺骗,选择从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一跃而下,因而进入了书中的“死无葬身之地”——一个没有墓地的灵魂们聚集的地方。
伍超从家中返回,听闻鼠妹的死讯后痛苦不已,说:“她不是因为我送给她假的iphone手机而死的,而是因为我欺骗了她……我真傻。”在极度后悔中,他选择了去卖肾,因为他身上没有钱给鼠妹买墓地。
有了墓地的鼠妹终于可以去安息之地了。书中对她前往安息之地之前的净身仪式写得特别美。鼠妹“像是进入睡梦般安详”地等待净身;苍老的骨骼用双手合拢的树叶之碗舀起河水为鼠妹净身;经常围成一团的三十八个骨骼分开去用树叶之碗舀水,发出了触景生情的呜咽声;谭家鑫安慰哭泣的女儿“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在哪里都一样”;张刚和李姓男子虔诚地将河水洒向鼠妹身上的青草和鲜花;身穿白色衣衫的李月珍带着27个婴儿来了,青草弄痒婴儿们的脖子,他们发出了咯咯咯的笑声。
我读这一条主线的时候想了很久。我首先想不明白为什么伍超说什么也不愿意出去工作,其次不理解他们为什么都如此冲动——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然后我恍然大悟:是的,在他们看来,没有别的办法。
鼠妹和伍超的悲剧,是他们自身经历、想法和思考方式的局限决定的。他们被轻易地困在了一个个根本不是死角的地方,明明扭头就是路,却目力不能及,最终双双辞别尚有无限可能的世界。
文化资本重要吗?重要,因为它们是原本的家庭砸下资源培养出来的。没有它们会怎样?要看各人造化与悟性。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不完全在于它可以传递阶级身份。一个原本就很有钱家庭的孩子,就算是不学无术、醉心抖音、拒绝为社会或自己创造“价值”,难道ta就因此失去自己的阶级身份了吗?
不会,阶级首先来自于财富积累和社会地位,其次才是软文化的再生产。我相信有一部分读者看到前文列举的三个新要素的时候,已经嗤之以鼻过——“这不就是高级打工仔的秉性”“再有内驱力又怎样,一辈子也当不了老板”。
是的,文化资本不是决定性的,它更像是buff,能让人更好地适应规则、融入环境。
但是,我从鼠妹的故事中想到,所谓的文化资本中的很多东西,对个人生活也是重要的。比如定下心来分析局势、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的能力,比如外面的世界会更精彩的信念、爱与被爱的艺术……这些东西,会帮助人们更好地走好自己的路。
前段时间有个短视频文案特别火,叫“xx岁后我又将自己重新养了一遍”。我对这样的语言没有任何推崇,但放在这里,居然和本文的意思是可以吻合的。
好的文化资本,是一部分家庭会努力提供给孩子的(他们也可能失败,因为教育是个复杂的过程)。这些东西有重要之处,但不是为了“跨越阶级”、宣扬出身论,也不是为了让一部分相似的人画地为牢,组成一个个的小团体。
关键的是,其中的一些东西,是有助于灵魂的滋养的,开阔的人生观念能让我们免于鼠妹式的悲剧。
而且,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就能给。